2012年4月21日下午,北京中华吟诵学会副秘书长朱立侠和办公室主任赵志军,在吟诵同仁叶金欣先生(温州戏剧界前辈叶曼济先生公子)的引领下,光临寒舍,对我的古诗词方言吟诵进行了全程录像(此前温州图书馆的三位同志也曾来采录过)。而后,徐素容、陈胜武和叶金欣诸君专程前来与我切磋、交流技艺,让我重拾五十年前对方言吟诵的兴趣。我生于瑞安,长于温州,历经70多年,未曾长时间离开故土,因而操一口地道的方言,会说瑞安话,也会说温州话。1959年,我就读于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,每逢寒暑假下乡采风,都收集到不少民歌、民谣,积累了丰富的方言素材。此后,受到本土老师的熏陶,逐渐学会了用方言吟诵古诗词。
承 师
教我《中国文学史》的是游任逵(1917—1986)老师。他原籍瑞安,抗战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,博闻强记,国学功底深厚。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时,游老师让我们选读的作品是南朝民歌《西洲曲》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描写爱情题材民歌的扛鼎之作,朱自清先生在他的名著《荷塘月色》里曾引用《西洲曲》里的佳句“采莲南塘秋,莲花过人头,低头弄莲子,莲子清如水”。游老师一边精细分析作品,一边情不自禁地微闭双眼,以略带沙哑的嗓音轻轻地摇头吟诵,博得满堂掌声。他还教我们用方言掌握平仄。他说北京人平仄不分,我们温州人保全丰富的古音韵,用方言一读就能分得清楚。温州方言从古声调的“平、上、去、入”入手,一个字的读音可分为清浊两组八个声调,如:“东”字,其清声调按“平、上、去、入”可读作“东,懂,冻,咚(方言,打锣鼓‘咚咚锵’)”;浊声调“铜,桶,洞,峝(方言,木桶和地面的撞击声)”。取其“东、铜”清浊两字为平声,其他六字“上、去、入”均为仄声。就此反复诵读,便顺利地掌握了四声;久而久之,把《西洲曲》也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后来懂得“仄”声短促,“平”声 舒展的规律,诵读韵文,自然就余味无穷。游老师的办法真灵验。以后我把这办法传授给喜欢古诗词的朋友,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古诗词的创作。
另一位授业老师叫翁达藻先生。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执教于复旦大学,并任过《浙江日报》总编辑兼主笔,通今博古,学术水平很高。后调入温州师范学院,教我们《中国通史》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到温州演出。演员们为了提高文化修养,利用业余时间到温州师院与师生们进行朗诵艺术交流,翁老就给他们讲吟诵艺术。讲到兴头上,他就起立摇着花白的长胡子,用脚板敲地高吟毛泽东的诗词“人生-易-老--天--难-老,岁岁--重阳--今又--重阳--,战-地-黄花--分外--香……”翁老的“脚板敲地吟诵”忽然使我想起李白的《赠汪伦》“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,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原来古人吟诗也有“踏歌”一举。于是我就模仿翁老的“人生-易-老--天--难-老……”用脚尖打拍子吟诵起来。
再者,就是聆听杭州大学宋词宗师夏承焘先生给我们中文系讲宋词。他诵读李清照的《如梦令》全是用杭州官话和温州方言混搭的“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?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。”其中特别是“风骤”的“骤”,“残酒”的“残”,“海棠”的“棠”,以及“依旧”的“旧”发音都是采用浓重的温州方言的浊音,听来尤其入耳。往后就模仿夏先生的方言诵读了。
还有,王阜彤先生给我们开《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研究》课。每逢讲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古典诗词,他也会带着浓重的平阳方音吟诵,给我们以启迪。
尝 试
受诸位老师的影响,我对古诗词的吟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除用普通话吟诵外,也常用方言吟诵。方言吟诵的音韵特别悦耳,如《西洲曲》的开头“忆梅下西洲,摘梅寄江北,丹衫杏子红,双鬓鸦雏色”其中“北’和“色“两字“普通话读上声“bei”和去声’se”,不通韵,而瑞安方言中的两个字却都读仄声里的入声,并同韵,读来耐人寻味。
我在吟诵的过程中,熟练地掌握了仄起平落的声调变化和七言四拍,五言三拍的节奏规律。久而久之,觉得自己的吟诵千篇一律,单调乏味。中国古典诗词非常讲究意境和情感,如果不同的诗词,赋予不同的吟诵声腔,是否更加有情趣呢?老先生们的吟诵缺乏一定的音乐性,能否在其基础上做些改进呢?如,宋词范仲淹的《渔家傲》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,反映作者守卫边疆功业未成而思乡情切的矛盾心理,我尝试把积累的民歌、民谣音乐素材揉进吟诵中,反复实践,形成以下旋律—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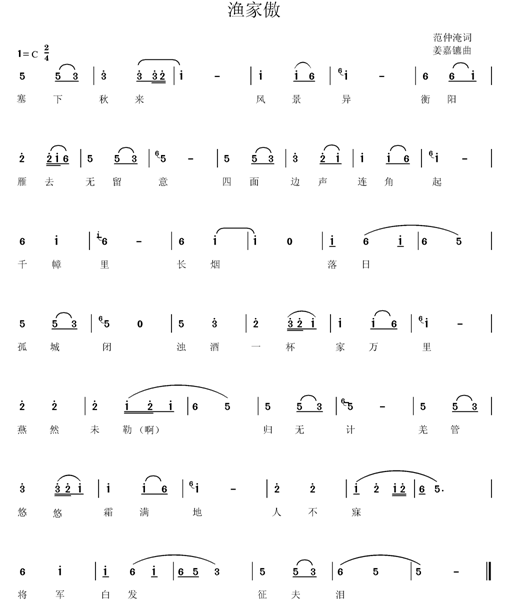
按此旋律吟诵,可把秋到边塞,北雁南归的意境展现出来,而且作者长年驻守边疆、功业未立、归思难收的“将军白发征夫泪”的悲情也得以恰到好处地表现。
对于击拍踏歌的吟诵,我的体会是,更适宜于豪放、潇洒情緒的表达。如苏东坡调寄《江城子》的“密州出猎”,描述的是作者在山东诸城任太守时,率众出城狩猎的盛事,气概豪迈,场面热闹。如试用击拍踏歌的节奏来表达“老夫-聊发-少年-狂,左牵-黄,右-擎苍,-锦冒-貂裘,-千骑-卷平-冈。为报-倾城-随-太守,亲-射虎,看-孙狼。 酒酣-胸胆-尚-开张,鬓-微霜,又-何妨!持节-云中,何日-遣-冯唐?会挽-雕弓-如-满月,西北-望,射—天狼----”这样的节奏,加上通韵的方言(瑞安话或者温州话)“狂、黄、苍、冈、狼、霜、妨、唐、望、狼”更能表达酣畅淋漓的情怀。反之,他的另一首同一词牌《江城子》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,则是一首悼亡词,抒写梦中与去世十年的妻子相见的悲惨情景,体现了作者对妻子永志不忘的深挚感情。这样的词只能带着忧郁的悲情去吟叹,如果用击拍踏歌的节奏去吟诵,那就适得其反了。
总之,温州方言保存了丰富的古音韵,在中国汉语言中是不可多得的活化石。中华吟诵学会负责同志为建设中华吟诵数据库,不辞劳苦前来寒舍进行采录,令人感动。为中华吟诵学会进一步开展吟诵推广交流活动,我特写成以上体会,就正于业界方家和吟诵爱好者。
(姜嘉镳/文 温州大学报20120930/来源)